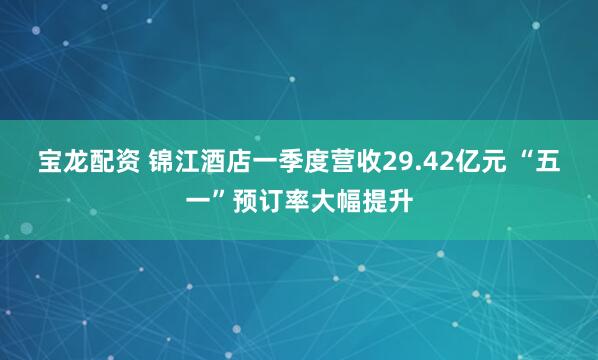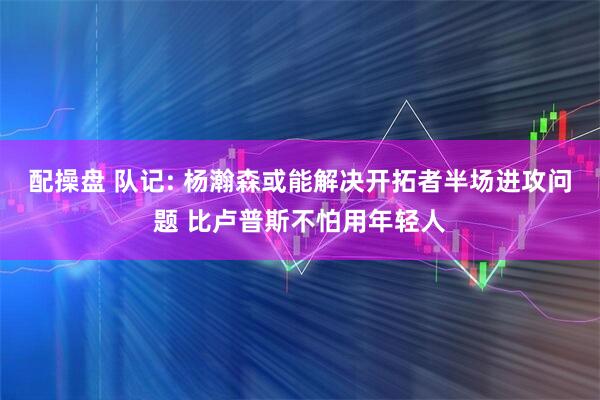【1955年8月大牛时代配资,北京中南海】“这份名单,我看还得改一改。”毛泽东放下钢笔,指尖在纸面轻轻一敲,旁人愣住——被连夜划掉的名字,正是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。
那一年,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。、邓小平所部的二野高级将领名单刚送上去,负责整理材料的秘书心里有底:张际春稳拿上将。然而,当最终公示稿下发时,张的名字消失了。军队里议论纷纷:三号首长去哪儿了?

张际春的传奇,从一张旧学籍卡说起。1900年,他出生在湖南宜章,家贫,却拼命求学。六岁进私塾,十七岁考进县高小,中间多次因学费辍学。生活艰难,但那副“必得读完书”的倔劲儿,伴了他一生。
1920年春,他背着行李到长沙,成为省立湖南第三师范的新生。也是在那里,第一次近距离聆听毛泽东讲社会主义与农民运动。讲堂窗子开着,春风扑面,年轻人猛然觉得,自己眼前的路不只通往教书匠。

不久大牛时代配资,毛泽东领导湘区工运,罢工、罢课此起彼伏。张际春跟着走上街头,写传单、喊口号、搞夜校。1926年北伐风起,他正式递交入党申请,被批准在宜章组建农民协会。这一年,他二十六岁。
“四一二”后的白色恐怖逼得地下党一夜换了天地。张际春辗转山乡,协助朱德、陈毅在湘南起义。起义队伍上井冈山时,他肩扛步枪、手提油印机。毛泽东再见到他,说了一句:“老同学,一起干到底。”
留在井冈山,他被派到王佐、袁文才的地方武装穿针引线,做政治工作。后来回忆:“张际春拿着马灯挨连队走,连锅里缺盐都知道。”这种“知兵、知心、知底”的作风,日后成了二野政治工作的底色。

红一方面军成立后,他调任政治部宣传处处长。短短一年,先后到四个师任政委。频繁调动并非折腾,而是毛泽东对他的磨砺——让他在不同部队推广统一的政治教育方法。张际春没辜负信任,每到一处就办夜校,编“小唱本”,士兵们管那玩意儿叫“张政委的口袋书”。
长征途中,张际春被抽调到红军大学任政治教员。讨饭、爬雪山、过草地,他仍坚持天天讲课。有人抱怨:“边走边学大牛时代配资,能学到啥?”他抬头看雪线:“走不动时,知识能当干粮。”硬是把半截粉笔、几张报纸撑出一所“流动课堂”。
抗战时期,他在延安抗大一干就是七年,从教育科长到政治委员。后来许多共和国大将、上将见了他还喊一声“张政委”。这种“双重身份”——教育者与战区政工首长——让他既懂课堂,也熟沙场。

进入解放战争,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。那趟行军,十万将士冬衣告急。刘伯承急得直跺脚。张际春却从民间小作坊找灵感,发动连队自纺自缝。几十万件棉衣在半个月里做完,且银钱与布料皆按价付款。战士打趣:“张三号,不仅能打仗,还会‘裁缝’。”
渡江战役后,二野大军进西南。重庆曾是国民党陪都,黑帮、散兵、失业者交织成一锅粥。张际春兼任军管会主任,第一个动作就是恢复供电、发粮票,随后整合新闻纸、广播台,一边肃匪,一边安民。他写给中央的2000字报告,被邓小平批示“写得好”,毛泽东也原文圈点,称“形象、生动”。
如此资历,为何不授衔?原因不复杂——毛泽东把他调往中宣部,任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主任,希望把“军队政治工作那股认真劲”带到地方。张际春直言自己“外行”,毛泽东摆手:“你是老政工,对宣传不是外行,是换个战场。”

从穿军装到着便服,他没带走一名秘书,进京后一头扎进文件堆。文化战线人多嘴杂,他依旧“井冈山作风”:调研、开座谈、跑基层。一次部队展览将他与刘伯承、邓小平三张照片并列,他当场让撤掉:“二野里,刘邓是主心骨,我靠边站。”
遗憾的是,1966年后风云突变,他遭受冲击。1968年病逝时,家属只找到一本磨损严重的旧笔记本,封面写着八个字:讲真话,做老实人。

1979年,全国政协礼堂庄严肃穆。邓小平主持追悼会,评价张际春“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,党的宣传战线的好干部”。在场的老二野人默默起立,军礼、鞠躬,泪水没遮掩。
1955年那个淡淡一划,让张际春从将星之列转身进入另一条战壕。有人替他惋惜,更多人佩服他的服从与清醒。军衔可以被划去,但历史不会抹掉他曾带来的那股真诚、倔强与周全。
大牛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